时间:2022-01-13 10:14:12作者:沙漠一只雕来源:网友整理我要投稿

1
2017 年 8 月,我参加了一个语文课堂观摩活动,听了一位特级教师执教的《答谢中书书》。
这位教师先花了 20 分钟带着学生逐句翻译课文,并提出了译文的标准:信、达、雅。
学生译,译得自然不够“雅”,于是教师出具自己的“雅译”,如“山川之美”的“美”译成“美丽”不雅,得译成“壮美”;“青林翠竹”的“青”,译成“青色”不雅,得译成“青葱”……对译文字斟句酌,反复推敲。
接下来又花 15 分钟,要求学生套用特定句式说出课文美在哪里。
最后 10 分钟终于开始读课文,教师告诉学生,读书要忘我,要声情并茂,还要读出层次,读好某个字某句话……但如何读好,没说,于是草草读了两三遍了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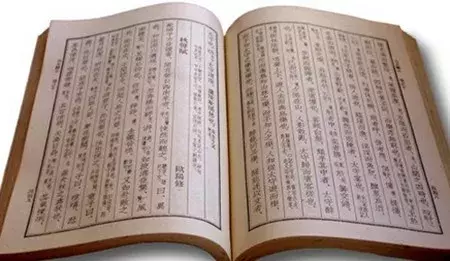
一节课下来,学生一个个兴味索然,没精打采;课后,几位点评专家也对这节课颇有微词;在场的一些听课教师也议论纷纷:“文言文怎么能这样教呢?”
那么问题来了——文言文该怎样教?
我想起了张必锟先生。
2
张必锟先生是语文教育界的老前辈。他 195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曾在北京的多所中学执教,20 世纪 80 年代起参与编写人教社的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参,一编就是二十多年,有人戏称他是“人教社中语室的第一代长工”。
2016 年,《我教语文——张必锟语文教育论集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,我有幸担任本书的责编。先生以文言文教学见长,书中近半内容与此相关,涉及诵读教学、阅读能力培养、背诵训练、虚词教学、教材改革、考试复习等各个方面,有理论探讨,也有实践示例,内容相当丰富。
(点击“阅读原文”可购买此书)
讨论书稿的编次时,先生嘱咐,要把《学文言非诵读不可》放在正文第一篇,因为这是全书的纲领。文章篇幅不长,却要言不烦地阐明了为什么要诵读、诵读的量、诵读教学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进程等关键性问题。
为什么文言文教学要以诵读为主?主要是为了培养语感。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离不开语感的培养。
语感首先来源于听和说,需要“活”的语境;文言虽非供听说,却可以通过读来补救。“读来读去,许多词、语、句、篇都成了自己语言仓库中的一个部分,对文言的表达方式和表达习惯定能逐步熟悉起来”,语感就是这样通过诵读一点一点积累、培养起来的。
先生还批评了文白对译和语法分析这两种教法的弊端:
“译几个难句固属必要,但通篇一句不落地译了出来,往往使初学者‘得鱼忘筌’,把注意力倾注在译文上。
而讲所谓‘动宾倒置’‘定语后置’‘取消句子独立性’之类的规则,则无异于给刚学会唱歌的儿童讲曲式结构和共鸣原理,只能使初学者如堕五里雾中;
因为所谓语法规则都是从大量的具体语言现象中概括出来的,不熟悉具体语言现象,即使你讲得正确无误,学生也未必真正理解,更谈不上实际运用……
这样来教文言文,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,对培养语感非徒无益,反而有害。目前中学生对文言文的厌学情绪有增无已,不能说跟这种烦琐的教法无关。”
上述批评可谓一针见血。而早在 1983 年,先生就在《“对号入座”有害无益》一文中指出了对译教学的五大弊端:一曰目的不明,养成坏习;二曰内容烦琐,消化不良;三曰生搬硬套,损害原意;四曰机械训练,枯燥乏味;五曰增加课时,浪费时间。
遗憾的是,这么多年过去了,还有不少教师在课堂上大搞文白对译和语法分析,而且搞得扬扬得意。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教师,不仅要译,而且要“雅译”。
这位教师难道不知道严复的原话是“译事三难:信、达、雅。求其信已大难矣”吗?“信”,严复犹叹其难,如今却用“雅”来要求这些积淀尚浅的学生,这难道不是件十分滑稽的事情吗?
更有甚者,宁可让学生在课堂上齐声朗读作者介绍、课下注释、白话译文,就是不读课文,这学的是哪门子文言文?
究其根本,是他们对文言文教学目的的认识有偏差。有些教师教文言文,只着眼于应付考试——甚至都不是中考、高考,而是平时一些不正规的小考。
小考考什么?课内文言文的翻译和语法,于是教师就只讲这些,到了中考高考,再想其他的办法应付。而先生的眼光则要长远得多:
“我们教文言文,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培养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,使他们在毕业后能够读一点文言作品,以利视野的扩大和文化素养的提高——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就是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了。
既如此,什么是阅读文言文的理想境界呢?它不是能将文言文译成现代汉语,也不是能对文言语句做语法分析,而是一看就懂或者经过查字典、会意而后懂。”
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,确乎“非诵读不可”!
先生力倡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,并名之曰“诵读教学法”。
很多教师的文言文教学也包含诵读环节,但往往只是一个普通的、孤立的甚至流于形式的环节(近年来还有教师引入了吟诵、唱诵、念诵等五花八门的方式,迹近杂耍,而非教学)。而“诵读教学法”则是以诵读为最主要的教学手段,以此带动其他训练的展开,强调诵读与会意的密切结合。
很多教师生怕学生读不懂(更怕考试要考),非要逐字翻译,逐句串讲,讲完再读再背,自以为这就是“理解的基础上诵读”,实际上是将会意和诵读割裂开来了。先生则指出:
“学生读文言文而能会意,是毋庸置疑的。文言跟现代汉语同源而异流,同为主,异为次,此其一;其二,我们并非读经,课文里没有佶屈聱牙的句子,而又有标点,有注释,认真读读,至少也能读懂一小半。一小半懂得,就有了会意的基础。
会意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:一是心知其意而口不能言;二是知而能言,虽不中亦不远;三是言而能中,即所谓确解。……一篇之中,半数能确解;其余,或心知其意,或言而不中亦不远,均无不可,极个别语句甚至可以存疑。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,因为它给学生留下了继续会意的余地,使其倾全力于诵读,在诵读中求解,在诵读中感知文言的表达特点,在诵读中积累语言素材——从长远观点看,其效果比让学生借助完整的译文来了解文章大意要好得多。”
这就从理论上破除了对“字字落实,句句翻译”和“先译后背”的迷信。当然,想要从实践上破解,还需要改革我们的各级。
先生提出,应该灵活运用记诵三要素以达到自然成诵。三要素,一是“口熟”,即通过反复朗读,依靠对声音的直感来记忆;二是“利用支撑点”,是在粗知大意的基础上,以关键语句为支点将全篇贯穿起来;三是“掌握文章理路”,即理清各层次间的逻辑关系,从而水到渠成地顺畅背诵。如果只有“口熟”,那便还是“死记硬背”;如果只有理路分析,也很难快速成诵。只有三者有机结合,才是真正有效的“理解性背诵”。
在诵读教学的过程中,先生特别强调教师指导下的课堂诵读练习,其要点有二:一是指导必须具体,“因为读音涉及词义,停顿涉及句子的组织,语气涉及虚词的作用和作者的感情,读得正确可以反过来促进对文意的理解”;二是教师要起示范作用,“教师的领读特别是领背,是一种直观的指导方式,可以帮助学生正音、读出语气,并品味语句的内容”。先生自己就是这么做的,凡要求学生背诵的,他都先背给他们听;至于具体的诵读指导,在《我教语文》一书的“教学实践编”中就有丰富的示例。
3
一次从先生家谈完稿子回来,有同事问我:“必锟先生身体还好吗?”我说:“精神尚可,就是手抖。”同事听了哈哈大笑,说:“二十年前就抖!不过说来也怪,先生一上讲台就精神焕发,手也不抖了,说话也利索了,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”这说的是 1997 年先生在江西南昌铁一中执教《五柳先生传》的事情。
这堂课的实录收入《我教语文》一书的“教学实践编”。虽是实录,但篇幅很短,因为先生既非“满堂灌”,也非“满堂问”,甚至连词语解释、句意串讲的环节都没有,他在课堂上只做了两件事:一是激发兴趣,二是指导诵读。
为激发兴趣,他从学生学过的《桃花源记》导入,将其比作风俗画,再把《五柳先生传》比作肖像画,而且是作者的自画像;课上完了,他又因地制宜,当堂背诵《滕王阁序》(滕王阁就在该校附近),并提出殷切的希望,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热情。
至于指导学生诵读,则采取点拨与诵读相结合的方式,用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指导学生理解文章大意,用“加句”的方式理清了文章脉络,学生在此过程中读读背背,一节课下来,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基本成诵。
我想,这不就是“把课堂交给学生”吗?这不就是“活动式教学”吗?既能让学生兴趣盎然地“动”起来,又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(理解大意、梳理脉络、当堂成诵),这样的课堂在今天恐怕都不多见,与前面提到的那位教师更是判若云泥。
“当堂成诵”,这几乎成了先生的一个标签。无论去哪里讲文言文示范课,无论课文长短、学生基础好坏,都能做到这一点,这就是先生的“神奇”之处,也说明先生的“诵读教学法”确实行之有效。
我近年来参与统编语文教材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,负责两个古诗文单元,现学现卖,模仿先生的路数做了一些诵读教学设计。但毕竟才疏学浅,定有不少画虎类犬之处,只得留待日后慢慢改进完善了。
4
《我教语文》一书中也有关于现代文和作文教学等方面的内容,虽不及文言文教学的部分有特色,却也胜义迭出,足启教慧。
如谈郑振铎《猫》、老舍《小麻雀》,并不停留于动物形象本身,而是关注到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和作者的悲悯情怀;谈鲁彦《听潮》、高尔基《海燕》,将“诵读教学法”延伸到现代文和外国作品的教学中,并与审美教育有机结合;而从《阿Q正传》的教学引申出的“长文短讲”的问题,对于今天的阅读教学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又如写作,先生没有什么系统的理论,总体来看强调三点:一是勤练笔。先生认为“练笔”既能训练学生的语言和构思,而又简便易行,符合学生心理特征,因此提出“把课外练笔列入正常的教学计划”。二是多评改。书中收录多篇作文评改,均细致入微,切中肯綮。三是提倡“教师下水”。
王栋生老师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:“作文教学的问题出在哪里?百分之九十的教师自己都不会写文章。”先生则是一个正面的示范。书中的“诗文创作编”收录了先生的书评、散文、杂文、译作、对联、旧体诗等,均清通可喜,足资法鉴。如果每名教师都像先生一样乐写、善写,我们的作文教学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局面。
其余如《我的探求》《语文课的基本特征和我的教学实践》《谈串讲》《说“点拨”》《教学要求宜适当》《关键在于要养成认真读书的习惯》诸文,也都是建立在数十年教学实践基础上的笃实而深入的思考。虽然大都写于 20 世纪末,但今日看来仍能切中时弊,发人深思,令人警醒。
最后,我想说说先生的文风。全书文字绝不故作高深,亦无空言虚蹈,而是朴实无华,余韵悠长。一如本书极朴素的书名——《我教语文》——语文,不就应该这样朴素地教吗?
附记
2016 年 11 月 5 日晚 9 点半左右,我把刚刚从印厂拿到的《我教语文——张必锟语文教育论集》送到了北京华信医院的重症监护室。先生此时已经不能说话,本不高大的身形比两个月前我见到他时又瘦小了好几圈。医护人员把病床缓缓摇起,他斜倚着,看到了这本凝结了他大半生心血的专著,张了几下嘴,却发不出声音。先生的女儿突然叫道:“看!老爸笑了!”
护士们说,这是住院半个月以来,先生第一次露出笑容。
两个月后,先生溘然长逝。
我与先生同毕业北大中文系(我比先生晚了 61 年),相识不过一年多,打过一个电话,写过七八封信,连同医院那次也只见过三面而已,却常使我有如坐春风之感。
记得第一封信,先生称我为“恒舒先生”,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但先生随即解释说:“我对你的称呼是继承了我们共同的老前辈张璇(即张中行)先生的传统,他是 1935 年毕业的,我比他晚了 17 年,他一直称我‘先生’,我多次抗议无效,也就任他这么称呼,安然自若了。”
之后的来信中,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的一些想法总是赞誉有加,鼓励我大胆放手去做。后来的一次面谈中,他也向我说起北大和人教社的前辈当年是如何鼓励他的。我想,这或许就是所谓“薪火相传”吧!
版权声明:本站为兴趣小站,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请发送至底部邮件举报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。










Copyright © 2022 www.youhaowen.com 〖有好命网〗 辽ICP备2021011687号-1
免责声明:本站文章来自网友投稿,不代表本站观点,版权归原创者所有,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,请通知我们,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!